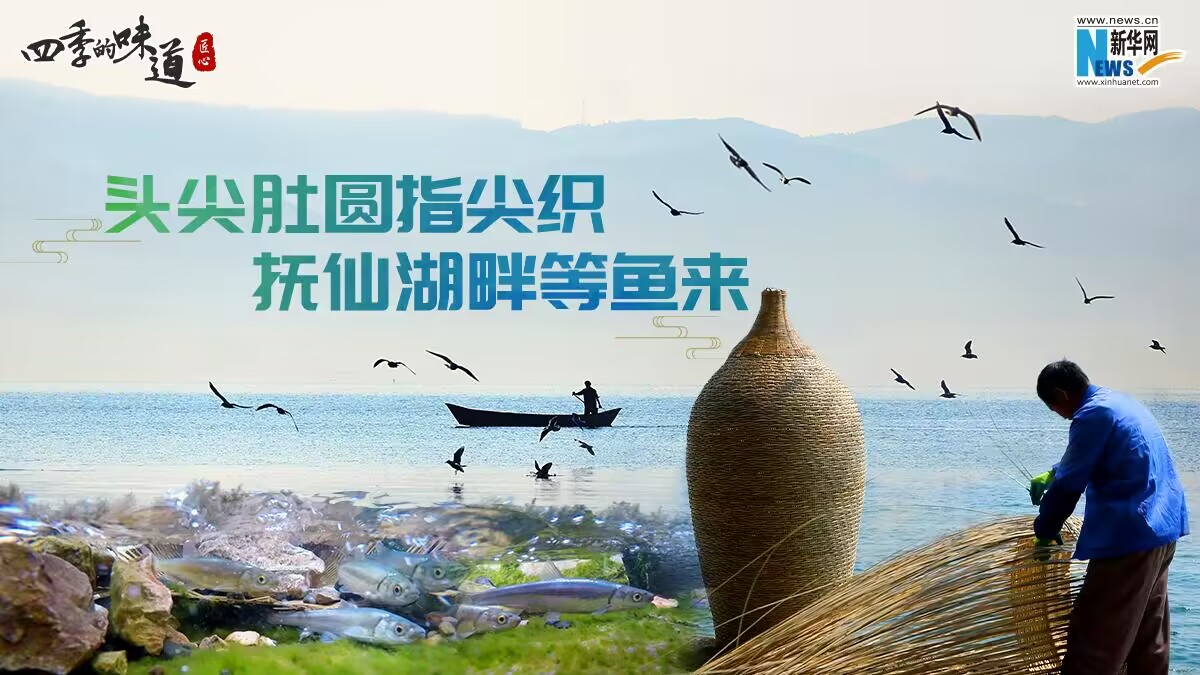四川農村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21.92%,已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勞動力短缺,“誰來種地”亟待破解
國家統計局四川調查總隊做了一項調查,在問及農業機械化推廣存在哪些問題時,649戶農機服務使用者中有50.1%的人認為農業相關配套設施不足;25.3%的被調查者認為使用環境和條件要求過高
龍橋社區農戶鄭玉仙說,她家中有5畝水田,卻分成零散的7個田塊,“把土地集中起來,規模化種田,農機才能下地”
在四川仁壽縣鐘祥鎮龍橋社區三社,2022年700多畝集中連片種植的水稻不久前喜獲豐收。在2021年,這些稻田由于缺乏勞動力,很多撂荒了。2022年,龍橋社區通過與農戶簽訂協議,引入農業公司統一進行規模化、機械化種植,解決了撂荒問題。
四川農村常住人口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21.92%,已進入超老齡化社會,勞動力短缺,與前些年相比,解決“誰來種地”越發迫切。
因為缺乏勞動力,一些老齡農戶自發對糧食種植結構進行了調整,“種近不種遠、耕沃不耕貧”。機械化對基礎設施要求更高,種地從人力到機器遭遇規模化瓶頸。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四川多地采訪了解到,一些地區通過土地流轉部分解決了種地問題,也有少數地方出現非糧化傾向。包括上述龍橋社區在內,一些地方嘗試通過社區集體聯合社等方式破解“單打獨斗”,實現規模化經營,四川農業生產方式正在孕育以規模化為導向的變革。
農村常住人口進入超老齡化
“2021年社區排查出400多畝撂荒地,農村人口老齡化,是土地撂荒的一個主要原因。”龍橋社區黨總支書記范冬說,龍橋社區三社有農戶500多人,在家的只有老人和兒童100多人,其中有“弱勞力”30多人。被視為“強勞力”的18至60歲健康男性幾乎沒有。
這樣的情況,在四川農村比較普遍。四川是農民工輸出大省,2021年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2682萬人,青壯年大多在外務工、定居城市。仁壽縣板橋鎮青龍社區黨委書記歐陽運清說,社區有1453戶、3725人,青壯年勞動力幾乎全部出去務工,留守在家的只有老人、兒童、殘疾人等1200多人。
農村年輕人多數不愿種地、不會種地。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新福社區農戶周群芳說,她的兩個兒子二十多歲,不愿種地,也不會種地,現在都在縣城工業園區的企業務工,家里的地由她自己和70多歲的老母親種。
現在,種地農民普遍在六七十歲。農村人口老齡化加劇,“誰來種地”問題凸顯。
按照國際通行劃分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時,進入老齡化社會;占比達到14%,為深度老齡化社會;占比達到20%,為超老齡化社會。
四川省統計局數據顯示,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四川65歲及以上人口為1416.8萬人,占常住人口比重為16.93%。比2010年上升5.98個百分點,比全國高3.43個百分點。2020年四川農村常住人口65歲及以上占比達到21.92%,高出全省4.99個百分點,已經進入超老齡化社會。
因為缺乏勞動力,一些老齡農戶自發對糧食種植結構進行調整,只耕種部分條件較好的田塊,一些離家距離較遠、缺乏灌溉水源、耕作難度大的田塊就放棄了,糧食生產主要滿足自家食用。
“我老伴68歲了,兒女都出去打工。過去幾年,家里的田只種了三分之一。”龍橋社區一名農戶說,他們縮小水稻、油菜種植規模,放棄種植紅薯等耗費勞力、非生活必需的作物。
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戶出售的糧食減少,部分農戶還要到市場上買米吃。在四川某農業大縣,當地農戶傳統上會占用半間房屋用石頭砌成糧倉,農戶俗稱“石柜子”,一般可以存放七八千斤稻谷。當地一名農戶說:“以前我們村里每家每戶都有‘石柜子’,最近幾年,村民幾乎全部砸掉了‘石柜子’,家里只存幾個月的口糧了。”

在四川省眉山市青神縣青竹街道季時壩村,村民給種植的玉米和大豆施肥(2022年4月19日攝) 王曦攝/本刊
田塊細碎 阻礙機器換人
農村勞動力短缺,人工成本走高。“農忙時節雇請村民,一人一天工資要120元,還要包吃、包接送,綜合下來人工成本已經達到140元一天,還不一定能請夠人。”眉山市東坡區浩翔水稻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李俊清說。
農業機械化受到土地條件制約。以2022年各地大力擴大種植面積的大豆為例,四川省農業農村廳數據顯示,2021年四川大豆的綜合機械化水平僅7.56%。
國家統計局四川調查總隊近期做了一項調查,在問及農業機械化推廣存在哪些問題時,649戶農機服務使用者中有50.1%的人認為農業相關配套設施不足;25.3%的被調查者認為使用環境和條件要求過高,不適合當地實際情況。
與北方平原地區普遍推行機械化的情況不同,在以四川為代表的一些南方地區,山區和丘陵較多,由于地理和經濟條件限制,部分地區沒有農機生產道路。同時,地塊細碎分散、形狀不規則,不能集中連片,坡多、臺多、田埂多。
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時,四川農戶靠抽簽確定承包地,一戶的田塊往往零碎分散在多處。很多村里都能找出一個斗笠、草帽就能蓋住的“斗笠田”“草帽地”。相鄰的田塊分屬不同農戶,各種各的,農作物種類都不一定相同,農機難以施展。
在青龍社區,歐陽運清指著一處農房后面不大的耕地說:“這塊地6分大小,分割成4家人的承包地,有些農戶一家人的承包地分散成七八處。”
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是未來發展趨勢。在眉山市東坡區修文鎮岳營村,高標準農田項目2021年11月開工,2022年春耕生產前建成。此前,當地農田是南方地區常見的小田塊,高低不平。項目施工包括平整土地、修建田間道路和灌溉溝渠等。
“以前澆水、搬運靠人挑,費時費力。”岳營村村民岳洪漢說,現在,田里通了水、通了路,小田改成了大田,既方便灌溉,也方便機械化作業,愿意到村里流轉土地的業主多了,流轉租金也有所上漲。
四川省目前要求各地在高標準農田建設資金保障上,中央、省、市、縣財政資金投入共計不低于3000元/畝。2022年,中央、省級財政投入合計為1500元/畝,還有1500元/畝需要市、縣解決。但市(州)級財政投入偏少,縣級財政投入“占大頭”。
高標準農田建設任務重的縣都是農業大縣,一般經濟不夠發達,籌措配套資金比較困難。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某縣一名干部說,對于2022年項目,阿壩州財政按300元/畝進行配套,縣級財政需安排1200元/畝的配套資金,雖然采取了整合各方面涉農資金集中投入等措施,但仍然比較吃力。
為解決配套資金不足的問題,一些地方正在嘗試用創新的辦法。在內江市龍門鎮龍門村,2021年10月建設銀行向村集體賬戶發放100萬元貸款。龍門村黨支部書記羅家元說,這是內江市首筆高標準農田專項貸款,主要用于村里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資金周轉。
2022年5月,遂寧市農業農村局和各縣(市、區)農業農村局分別與中國農業發展銀行遂寧市分行、農發行各縣支行簽訂合作協議。“十四五”期間,農發行將為遂寧市54.12萬畝新建高標準農田和39.6萬畝改建高標準農田提供信貸支持。
發行專項債券,也是各地正在開展的一項探索。農業農村部2021年9月印發《全國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2021—2030年)》,其中提出,鼓勵地方政府在債務限額內發行債券支持符合條件的高標準農田建設。記者從四川省農業農村廳了解到,四川積極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專項債券發行工作,將高標準農田建設項目新增耕地指標調劑收益,優先用于農田建設再投入和債券償還、貼息等。
孕育生產方式變革
在龍橋社區,當地干部試圖破解難題。“我們多次組織黨員干部、群眾代表開座談會,針對土地使用、農作物種植、農民種地意愿等深入調研。”范冬說。
農戶們普遍希望實現機械化,從而減少勞動力投入。但首先要解決各戶耕地“小而散”,農戶“單打獨斗”種田的問題。龍橋社區農戶鄭玉仙說,她家中有5畝水田,卻分成零散的7個田塊,“只有把土地集中起來,規模化種田,農機才能下地”。
農村的生產方式,需要更進一步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2022年以來,龍橋社區嘗試“黨總支+集體聯合社+公司+農戶”的新模式。簡單來說,就是由社區集體聯合社與316戶農戶簽訂土地入股協議,將農戶的土地集中起來,社區引入農業公司統一進行規模化、機械化種植,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農戶則可得到土地租金、經營分紅、務工收入等。
從“單打獨斗”到規模化經營,目前四川一些地方的情況正處于變革前的膠著狀態。近年來,一些工商資本下鄉,流轉農民的土地,實現規模化種植,但主要不是種糧食。記者走訪了解到,目前,流轉土地,種植葡萄、獼猴桃、柑橘等水果,一年每畝利潤可達數千元至2萬元,種植蔬菜每畝利潤也有2000多元。而種植水稻、小麥、玉米三大主糧,均處于微利狀態或虧損邊緣。近年來在四川流轉土地、種植草坪的重慶一家公司負責人朱波軍坦言:“一畝草坪的年產值可達1.5萬元左右,種糧食掙不了多少錢。”
在成都平原,目前土地流轉租金普遍為每畝每年“800斤稻谷的市價”,高的甚至達到“1000斤稻谷的市價”。而如果流轉土地種水稻,一年只能種一季,畝產才1200多斤,刨去土地租金、農資、人工等成本,收益微薄。即使冬春再種一季油菜,仍然掙不了多少錢。
一些地方對此采取了措施,為防止土地流轉“非糧化”,在土地流轉之初,就根據業主擬種植的作物,確定不同水平的租金。“如果業主種水果等經濟作物,租金就收1000到1200元一畝。如果業主種水稻、油菜等糧食作物,一畝租金就只按照550斤稻谷的市價來收,算下來只有700多元。”成都市大邑縣安仁鎮新福社區黨委書記胡永洪說,“我們這里農戶都清楚,人家來租地種糧食,你租金不能收高了,不然人家只能賠錢。你要是租金收高了,人家就種不了糧食了,只能種其他的經濟作物。”
崇州市某家庭農場負責人坦言,他種了20多年苗木,這幾年市場行情不好想轉行。現在政府要求防止耕地“非糧化”,他把80畝苗木都改回了水稻。不過,也不能完全靠種糧掙錢,他發展“水稻+小龍蝦”稻蝦綜合種養,實際上是靠養小龍蝦掙錢,每畝利潤能達到五六千元。
基層干部群眾認為,人口老齡化是當前四川乃至全國共同面臨的挑戰,是經濟發展和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對于解決今后“誰來種地”,他們建議:
首先,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培育更多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大邑縣旭成種植專業合作社職業經理人萬富旭說,吸引更多年輕人從事農業生產,關鍵是讓種糧“有錢可掙”,在保障糧食價格穩定的情況下,通過推廣優質品種、新農技,穩步提高糧食品質和產量,進而提升種糧效益。
其次,大力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實施耕地宜機化改造,提升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為土地流轉和規模化種植創造更好條件。
202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十二屆二次全會明確,逐步把全省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旱澇保收、能排能灌、宜機作業、環境友好、高產高效的高標準農田。“我們在守牢建好天府良田,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上狠抓落實。只有天下良田、才有天下糧倉,只有天府良田、才有天府糧倉。”四川省委農辦主任、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書記楊秀彬說。(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陳健)